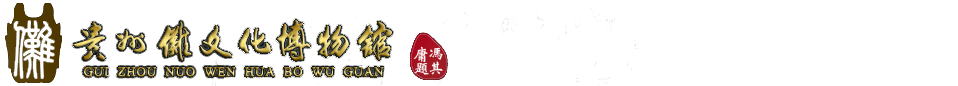“桃源”试论
时间: 2023-12-01 17:00:11 浏览: 68174黔东北苗族人民在还愿搬演傩戏时,巫师先要扎坛布景,布景工作的主体部分是扎“桃源洞”,以便用来安放傩母、傩公这两尊祖先神灵的木质雕像。在演出过程中,巫师要对“桃源洞”的形成、形状等情况作详尽的叙述,并有上、中、下“桃源洞”之说。
除搬演傩愿戏而外,在黔东北地区的苗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从丧葬仪式到求雨、追魂等仪式,从道具制作到祭祀用语的构成,崇尚桃树的现象比比皆是。所有这些,都是苗族远古时代桃崇拜习俗的反映,是苗族先民远古生活真实和纯朴的思想观念,经过千百年的演变沿传至今仍留存于民族共同生活习惯及宗教艺术上的遗迹,是一种文化密码,它与汉民族历史上曾奉桃木为“仙木”的意识观念有着实质上的区别。笔者不揣浅陋,意欲从上述尚桃现象溯求桃崇拜习俗的源头,以此反过来观照和解释苗族宗教、文化艺术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某些问题。请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一
黔东北苗族傩愿戏扎“桃源洞”是演出过程中一道必不可少的布景,“桃源洞”的形状、大小、色彩使用等方面一般都有较为严格的规定。具体做法是:巫师于所定还愿日期的头天来到主家,将两张八仙桌并排横放于中堂屋内,用粗细不等、长短各异的竹竿、竹片,甚至木条等材料作为骨架,在八仙桌上搭造形状如同的商立式洞子,从左往右数,第一、第五两个洞子高约l米,正中一洞高约1.1米(也有一些傩班把5个洞子扎成一样高),洞门上方仿照苗族传统住房的直檐式结构。整个洞身全部用彩色纸制作的各种剪纸图案进行裱糊和装饰,这些剪纸作品的图案、大小、色彩搭配均有一定之规。在举行“坐傩”仪式时,傩神娘娘在左,傩神爷爷在右,两尊雕像被分别供置在第二和第四两个洞子内,这两个洞子被称为“北海桃花山”(有的傩戏班子又称作“北海桃花源”)。在洞子的后面,分别悬挂着画有神像的卷轴式条幅画案,苗族傩戏画案一共5幅(有的傩班在门外“虚空”也挂一幅)。“桃源洞”是专门用来安放正神雕像或牌位的坛台,故称为“正坛”或“上坛”,与之相对应,八仙桌下设有“下坛”,又称“偏坛”,是用来安置五猖兵马的坛台。
在演出戏文唱词中,更为详细地叙述“桃源洞”有上、中、下三洞之分,分别用金锁、银锁、铁锁锁着,由张大郎、李二郎、矮满郎三位神将分头把守;在举行“开洞”仪式时,巫师要从上洞桃源请出
“先锋小姐”、“开山大将”、“算命先生”;从中洞桃源清出“和尚"“秦童”、“八郎”;从下洞桃源请出“土地”、“判官”,然后才正式演出折子戏。
据民间艺人介绍,建国前,还愿必具的“傩头”(傩公、傩母头部雕像),打洞求雨用的“小山”(高约10厘米的神将偶像,据说能夺关开道),冲傩追魂活动中“降童子”(用巫幻术使一个正常人神智
处于半昏迷幻觉状态,然后用红帕远远牵着让他领路给病人追索魂魄)用的弯木枷,以及祖师棍等须用桃木制成才有神威。到后来,桃木日渐稀少,不易得到,有的工匠便用其他木料代替,但“小山”和弯木枷非用桃木制作不可。除了搬演傩愿戏而外,涉及桃崇拜的现象在黔东北苗族人民的宗教信仰中屡见不鲜。某家死了人,要请巫师为死者举行“奖棍打”(意为“解除死神”)仪式,须用桃枝和水菖蒲叶煎水来给死者洗身,由头、颈、体而至下肢,按同样的顺序连洗3次。据说,用桃枝水洗身,死者的阴魂才能够顺着水菖蒲叶子尖尖所指的方向,到达祖先灵魂所在的东方故土。洗身之后,还要将桃枝水留下,待死者安葬入土后,用来为死者招魂。
一般认为,祖先崇拜观念产生于人类的氏族社会阶段。所有的氏族成员都相信他们出自一个共同祖先。共同祖先在氏族成员心目中具有元限崇高而神圣的地位,这就在原始初民的意识观念中直接促成了祖先崇拜观念的产生和祖先神(如苗族的傩神)的出现。对祖先神灵的崇拜与祭祀,普遍带有希望氏族(在后来可理解为同宗家族)昌盛、人丁繁旺的目的。可以看出,苗族人民自古以来还愿搬演傩戏要扎“桃源洞”,把自己最尊崇的民族始祖神——傩神安放在“北海桃花山”洞子内进行祭祀足以说明苗族人民在民族心理上,已经把桃与本民族的起源、生存、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苗族人民这种把桃视为一种与本民族贴近有本体力量的认识观念,与汉民族把桃当作一种只能镇邪驱鬼的异化力量的认识观念显然有着实质上的区别。在“奖棍打”仪式中,桃枝水可以帮助死者的亡魂顺着菖蒲叶尖尖所指示的方向到达苗族人民千百年来一直魂牵梦萦的“东方”故土。这也就更清楚地表明,桃代表着一种神奇的保护力量,它不仅可以庇护人类始祖,使苗族繁旺昌盛,还可以护送死者的亡魂回到祖先所在的极乐故园。 可见,苗族人民在共同的民族心理上,对桃的崇敬之情是何等的深切。桃在他们的心目中,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与本民族存亡兴衰息息相关的圣物,是一种图腾。
二
为什么苗族先民要崇拜桃,把始袒神——傩神安放在“北海桃花山”内进行祭祀?笔者认为,这一习俗与苗族先民在特定的环境下所经历的原始采集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地质考古及其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早先时候,黄河流域的气候要比现在温和、湿润得多,非常适宜于植物生长,这一带普遍生长着高大茂密的植物。勿庸置疑,这些高大的植物,其中就有暖温带重要水果——桃,依据史料记载可以得到证实:当时在黄河以南、江汉流域北部的广大地带,曾存在着大片的自生桃木,或在森林中间杂着大量的桃树。《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八日……弃其杖,化为邓林。”毕源注云:“邓林即桃林也,邓,桃音相近。……”《列子’汤问篇》云:‘邓林弥广数千里。’盖即《中山经•中次六经》所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矣。其地则楚之北境也。”《尚书’武成》记载:周武王攻灭了商之后,“乃偃武修文,归马华山之阴,放牛于桃林之野。”这里,华山之阳和桃林之野是同一个地方的两种称法。
隋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曾在今河南灵宝设桃林县。《辞海》①释“桃林”为“古地区名。又名桃林塞、桃源。约当今河南灵宝以西、陕西潼关以东地区。”
以上所引资料,既有神话典籍的记载,又有注释家的考证;既有古代王朝地方政治机构的设置,又有现代工具书所下的定义,这些不同方面的资料,却有一个共同之处,也就是指明了同一个地方--“河南灵宝以西、陕西潼关以东”,也就是毕源所注的“楚之北境”,或《尚书》所记载的“华山之阳”、“桃林之野”,在历史上确实曾经存在过一片“弥广数千里”的桃林。
从苗族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的形成、演变及迁徙的历史来看苗族先民桃崇拜习俗的产生,似应与这片桃林有关,与先民们在这片桃林曾经历过的原始采集狩猎生活有关。
采集、狩猎是人类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人们从自然界中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劳动方式。那时候,人们总是依林而居,或构木为穴,或寄身于林中的山洞内,过着“只知其母,不知其父”②的生活。在氏族内部,成员往往依据性别、年龄等形成原始自然分工,男子成群结伙外出打猎或捕鱼,女子则采集果实、菌类,相比之下,女人们的劳动收获往往比空手外出捕猎的男人们要稳定得多,数量也要多~些,她们对于氏族的生存与繁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在氏族内部受到普遍尊重,进而产生崇拜女始祖的形象。
苗族史诗和汉文献记载都表明,苗族最早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广大地区,在传说中的九黎时代以前,就已经历过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到蚩尤时期,父权制已逐渐确立,势力已逐渐强大起来,并与生活在西部、北部的黄帝、炎帝部落发生冲突,结果战败,首领蚩尤被杀,被迫退入“左洞庭、右彭蠡”③的荆楚一带。
显然,苗族先民在进入荆楚地域之前很早就在“楚之北境”(毕源语),即河南灵宝以西、陕西潼关以东的黄河南岸地区辗转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是正值“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那么,存在于那一片的大片桃林,就曾给苗族先民们提供过丰美的食物,提供过栖身的场所,剥兽皮为衣以御寒,拓山洞,搭树棚为屋以避风雨,处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童年时代”,这一时期,“人类栖止在自己原来的有限的地区里,以果实和坚果为食物,清晰的语言开始于这一时期。”④清晰的语言和一定的思维能力,增强了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并从自然界获得生活资料的能力,也使得在桃林里经历的生活景况得以留存在苗族原始先民朦胧的记忆之中。
三
当先民们因部落之争战败或因其他原因不得不离开曾为他们提供过丰美食物(桃子)的“乐园”之后,栖身于生活条件艰苦的新环境。他们就会极自然地怀念逝去的挑林中食物较为充裕的生活,这就是苗族桃崇拜习俗产生的最初的认识根源。
流传的湘西、黔东北一带的苗族史诗《Xeud bad deud mab》(音译为《鸺巴鸺玛》)就描述了苗族先民离开寅河寅尾⑤、厚吾厚西⑥,辗转来到占楚占菩⑦地界创造基业,重建家园,并举行了轰轰烈烈
的第一次鼓社鼓会的情况:
姊妹磋商,
兄弟作议;
商量要削筶祭祖;
商议要制鼓集会……
可以肯定的一种情况是,到达占楚占菩地方的苗族先民,在削答祭祖、制鼓集会活动中,由于所处时代距母系氏族社会尚不遥远,所祭祀的对象便主要是人类的共同始祖--女始祖;也由于在桃林中采果为食、构木为穴的漫长生活仍留存在先民们的记忆之中,那么,他们在鼓会祭祖时,便会供奉女始祖像,并用树枝搭棚扎洞子安放之,缅怀昔日穴居的女始祖并追忆在桃林中度过的丰裕的生活。这用来搭棚扎洞子的树枝,最初就极可能是桃树。在一种群体无意识状态下,苗族先民们载歌载舞以娱祖先和神灵,并将捕捞而得的鱼、虾,狩猎所获的猪、山羊等祭献于始祖神灵,祈求消灾纳福,这就是原始的傩祭活动。
由于在傩祭活动中,桃与祖先神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桃的地位就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在苗族先民的意识和信仰中,成为一种能保护人类始祖,驱邪镇恶,并能引导亡魂归返祖先所在的故土乐园的“神圣之木”,这就是桃崇拜习俗产生的最初的认识根源。
尚桃意识和桃崇拜习俗影响了苗族先民的原始宗教、艺术及日常生活诸领域。经历几千年而承传至今的苗族人民宗教、文化生活中的许多现象,除傩戏中扎“桃源洞”安放傩公、傩母外,死了人用桃枝水洗尸招魂,打洞求雨、冲傩追魂等活动用桃木偶像、桃木枷夺关开道,等等,都是古老的桃崇拜习俗的遗迹。
用桃树枝等材料扎洞搭棚安放神圣偶像来祭祀的方法,一直保留在苗族宗教活动中,举行还傩愿戏、和消愿戏、打洞求雨、冲傩追魂等等活动,都要扎洞安放神圣偶像,举行“农涅”(译成“吃猪”)祭祀活动时,用树枝扎洞子,将身着苗族女式服装的偶像安置在洞内,象征古代穴居的女始祖,其中在吃“抓抓肉”时,所有的人都不拿筷子,只用手抓着吃,每人面前还放着用篾棍串着的一小串猪内杂,表示带回去让家里那些仍躲在山洞里不能出来参加“吃猪”的老弱妇幼分享。不过,由于苗族历史上曾举行过无数次迁徙而不断更换生活环境,到后来,在举行这类祭祀活动时,扎洞所用的树枝已不再严格地要求必须是桃树枝,而可以是任意一种树木以致用纸剪成各种图案来代替,但仍叫做“桃源洞”,其中用来安放傩公、傩母的两个洞子也仍叫做“北海桃花山”或“北海桃花源”。
至于“桃源洞”内的神像,也由于苗族先民在祖先神灵崇拜产生发展时期各部落先后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父权制逐渐占统治地位,这种现象反映到原始宗教信仰中来,祭祀对象就由单一的女始祖神,逐渐发展成一男一女的始祖神,承传至今,除“农涅”祭祀活动仍供一尊女始祖像而外,其余须扎洞安置神灵的祭祀活动,所供奉的神灵都是一男一女,即傩公、傩母。不过,据苗族巫师说,傩公一般不管事而只知喝酒,凡事都由傩母来过问,如主家缺儿少女,只向傩母许愿祈求,病人能否康复,何时康复,也只向傩母叩问。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在松桃苗族傩坛上所见到的“桃源洞”,以及在“奖棍打”仪式中用桃枝水给死者洗尸和招魂,某些祭祀器物必须用桃木雕刻等现象,都源于苗族先民远古时代所独有的桃崇拜习俗,而这种习俗的形成,又与苗族先民母系氏族时代曾长时间生活在拥有大片自生桃林或问杂大量桃树的森林地带——“弥广数千里”的古桃源,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
在这里,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苗族在宗教信仰及日常生活等方面存在崇尚桃木的习俗,汉族史籍上也有关于桃木是“仙木”的记述,究竟谁是源,谁是流?二者的关系又如何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需简略地回溯一下苗、汉两个民族作为独立的“人们共同体’最初形成及迁徙的大致过程,就不难得出结论。
我们知道,苗族是一个几乎与汉民族有着同样悠久历史文化的古老民族,形成后来汉民族主体部分的原始先民在渭汾流域、黄河上游及今天的西北广大地区活动的时候,苗族远占先民也在黄河中下游、中原一带活动了,它们各自在自己的活动地域内度过了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后来,汉民族各部落逐渐向东向南推移,并占据了中原地区,苗族不得不退入洞庭湖、古云梦泽为中心的荆楚地界,在这过程中,各氏族部落先后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阶段。
可见,以采集作为获取食物重要手段的母系氏族阶段,苗族先民正好是在“楚之北境”的大片桃林中度过的,而汉民族主体先民母系氏族时期的活动地域则远离古桃源,因而桃崇拜习俗不可能产生在汉民族中。
苗族主体先民退入荆楚地界之后,各部落相互联合,结成强大的“三苗”部落联盟,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古代文化,后来楚族各部在此媾础上吸收华夏文化而复兴苗族文明,形成了博大恢弘的“巫楚文化”,它包括大诗人屈原等人创造的《楚辞》为代表的楚国官方文化和“尚鬼”、“重典祀”为特征集祭祀、巫术、苗族医药等方面为一体的民间文化。“巫楚文化”对各民族包括北方汉民族的文化形成了极大的影响,也许就在这种文化大交流的背景下,苗族的桃崇拜习俗传到汉民族中,但是汉族始终没有崇拜桃木的风俗产生,只把这种从别的民族(苗族)中流传来的文化现象附会在本民族的神话之中,并以道教仙道观加以阐释,最早见于《淮南子-诠言篇》:“羿死于桃 。”高诱注:“ ,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同书《说山篇》:“羿死桃部,不给射。”高诱注云:“桃部,地名;羿夏之诸侯有穷君也。”其实,“桃部”就是“桃 ”,因《淮南子》为刘安众门下所编、人多手杂加上所采资料繁博而辑录致误,部字形相近,它们在汉代中原语音系统中是同韵字。无论是《淮南子》把桃与本民族神话扭和在一起和就法,还是高诱把神话传说中的人与物同具体的人、地名对号入座而得出鬼畏桃是因羿死于桃枝之下的结论,都明显带有牵强附会之嫌。以后辑书注释诸家,不辨真伪,以高诱之讹传讹,宋代便有把春联称作“桃符”者。《太平御览》九六七引《典术》:“桃之精生在鬼门,制百鬼,故今作桃人梗著门以压邪,此仙木也。”《说郛》卷十引马鉴《续事始》:“《玉烛宝典》曰:‘元日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即今之桃符也。其上或书神荼、郁垒之字。”从这些材料可知,在当时的汉民族习惯里,桃木纯粹是制鬼压邪的“仙木”,其作用相当于传说中的门神、郁垒、神荼,或者用来护门的桃木就是这两位门神。与之相比,桃在苗族人民心中的地位要高得多。从古至今,在宗教信仰及日常生活渚方面,存在着基于全民族深层文化心理意识之上的桃崇拜习俗。可见,汉民族在历史上曾把春联称作“桃符”,把桃木制作的人作门神以压邪,以及汉史籍上对桃木为“仙木”的零星记载,都是受苗族桃崇拜意识习俗影响而.出现的,这是汉、苗两个民族历史上文化、宗教信仰及其他各方面相互影响的有力见证,是中华大家庭各民族共创历史的最好说明。
五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搞清楚,苗族作为一个拥有800余万人口的大民族,分布在几个省区和世界近十个国家,为什么惟独黔东北及湘西部分地区的苗族人民至今仍保留着浓厚的桃崇拜习俗,而居住在其他地区的苗族人民其桃崇拜意识已不太明显了?为什么黔东北土家族人民举行傩堂戏还愿时也要扎“桃源洞”?它与苗族桃崇拜习俗有什么关联?
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有必要回溯一下黔东北、湘西地区苗族作为“人们共同体”形成的过程,有必要考察他们历史上和现时代所生活的文化环境。
约在公元前2500年,华夏氏族从西、北移人中原,同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发生冲突,蚩尤被杀,九黎瓦解并退入“洞庭”、“彭蠡”地界,与荆楚一带其他南蛮部落杂处,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
势力强大的“三苗”部落联盟。《国语•楚语下》有“三苗”“其后复九黎之德”的记载,说明“三苗”即属九黎或由九黎发展而来,北方华夏氏族一直把“三苗”视为心腹之患,不断发动战争武力征讨,“三苗”联盟最后分化,一部分联合楚族建立了楚国,后来统一了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并逐渐与华夏族融合;另一部分则先后避入鄂、湘、川、黔交界的武陵郡五溪地。汉代称为“武陵蛮”、“五溪蛮”,明代称为“红苗”。⑧《松桃厅志》记载:“松桃自古为红苗巢穴。”居住在黔东北、湘西偏僻山地的苗民,有些在民国前仍被称作“生苗”。所谓“生苗”,就是没有开化,未接触汉文化或汉化程度不深的苗族人民。
苗族是一个历史上举行过无数次大规模迂徙的民族,但黔东北、湘西苗族与迁往黔东南、黔西北、滇、桂等地以及老挝、泰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苗族相比,其生活环境是相对稳定的。他们
自“放驩兜于崇山”⑨以来,就一直在武陵山地生息繁衍,《松桃厅志》说松桃“自古为红苗巢穴”是准确的。几于年来生活在这里的苗族人民,除不断遭受汉族统治者的武力征讨外,生产、生活、文化等各方面基本上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境地。恰恰是这种近乎封闭的环境,使苗族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基本保持其原貌或按自身风格发展。正是这个原因,流行于黔东北一带的苗族傩愿戏,自原始傩仪、傩舞产生并发展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祭夹戏形态,虽历几千年,其戏剧成分仍较少,风格仍保持着粗犷古朴的特点,当中还留存着许多古老习俗和原始思维的印迹。本文讨论的苗族桃崇拜习俗,就是这种印迹在苗族傩愿戏、丧葬习俗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古老的桃崇拜习俗最终在黔东南、滇、桂等地以及其他国家的苗族人民中淡化或消失,则是因他们在历史上迁徙行程更远,时间更长,环境更复杂,同汉族及其他民族接触更为广泛而造成的。一个民族,由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出现传统文化此存彼失、彼兴此衰的现象,这在文化发展史上屡见不鲜的。比如,苗族芦笙文化在湘西、黔东北基本消失了,而在黔东南则得到承传和发展;同是黔东北地区,花鼓舞在松桃坡东一带仍盛行,而在坡西苗区已基本消失。
至于黔东北沿河、德江等县土家族傩戏也要扎“桃源洞”,完全是同一地域内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发展的结果。前面说过,历史上苗族各部落联盟并一度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原始文明,这种文明到后来因楚国的强盛而得到复兴并形成博大精深的“巫楚文化”,在当时和后世几乎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南方各民族文化的发展。
就在古“三苗”文明兴盛时期,在苗族先民生活的中心地带古云梦泽、洞庭湖平原的西南侧,也就是鄂西清江流域、川东、湘西北广大地区,濮、奴、苴、共等部落早已在其间活动,后来,其中的巴人融合其他部落建立了巴子园,并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民族“毕兹卡”,也就是今天的土家族。在苗族退入崇山及五溪地之后,巴人也受到楚国统治者和北方势力其中主要是秦国势力的多次打击。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司马错进攻巴蜀并夺得巴地,仡廪部族(廪君为首的“毕兹卡”部族)有的降服,有的南迁西退而与苗蛮杂处,在宋代出现了一些较有实力的大姓强户,甚至控制了苗族居住的局部地区。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苗族、土家族人民在同一地域内共同劳动、生息,他们在经济、文化各方面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往,土家族的纺织、刺绣工艺技巧就曾直接影响苗族的挑花刺绣;苗族医药、武术就受土家族人民的重视。我们今天在宗教祭祀活动中,看到土家族傩堂戏也像苗族傩戏一样扎“桃源洞”的现象,就是两个民族长期的文化交往的结果。值得指出的是,两个民族的傩戏“桃源洞”其形状、大小高度以及各洞名称都不尽相同,尤其是扎洞的剪纸作品,在图案、颜色使用、贴挂位置和制作技巧等方面,差别都较大。拙作《苗族傩戏剪纸艺术发微》⑩对之作了粗略的比较和分析,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结束语
通过对苗族现实民俗现象的考察并映证与之相关的史料记载,我们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生活在黔东北、湘西的苗族自古至今有着崇拜桃的观念和习俗,而这种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苗族先民远古生活真实反映在民族深层心理意识上的产物;搬演傩愿戏并将傩公、傩母安放在“北海桃花源”内加以祭祀,也绝不是一种孤立的民族现象,它是苗族傩巫文化构架中的有机部分,是一部活的民族文化史籍。可见,任何一种文化观念和形态的产生与发展,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不是“环境决定论”的翻版,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物质决定意识”基本原理的具体体现。
苗族尚桃意识和桃崇拜习俗形成之后,随着民族问的交往而传人汉族、土家族,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宗教、民俗等方面产牛了一些与桃有关的现象,但它们只是流而不是源。理清了苗族桃崇拜习俗产生及传承的线索,就可以解释苗族宗教、文化、民俗中的许多现象,如前面所说的用树枝扎洞祭祀女始祖,还愿要扎“桃源洞”安置傩公、傩母,吃“抓抓肉”,等等。以此为起点,我们可以窥探博大精深的苗族傩巫文化及整个传统文化的内涵。从而为促进苗族成为一个开放的民族,推动苗族文化的发展、兴旺,提供一种认识方法和思考路子。(吴 国 瑜)
注释
①<辞海>,缩印本,130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②(庄子•盗跖篇)。
③<史记•吴起传)。
④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页。
⑤苗语地名,传说指黄河中下游某地。
⑥苗语地名,古代楚国某地,详细待考。
⑦苗语地名,古代楚国某地,详细待考。
⑧<明史记事本末•补编卷四•西南群蛮》。
⑨《尚书•舜典》。
⑩吴国瑜:《苗族傩戏剪纸艺术发微》,载于《贵州民间工艺研究》,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