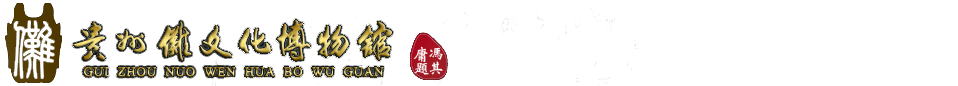试析边墙外围苗区傩戏“阴盛阳衰”的原因
时间: 2023-12-01 16:56:19 浏览: 65128边墙外围苗区,在改土归流之前被称为“生苗”之地。“生苗”是宋代至民国前期对居住在湘黔交界地尤其是松桃全境及铜仁部分地区苗族民众的习惯性称呼,在明朝万历年间官府修筑边墙(南方长城)以后,“生苗”被隔绝在边墙外围地区,长期处于“化外之民”的地位。时至今日,原“生苗”区的文化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反映在戏剧艺术方面,我们发现这一地区阴戏非常繁荣而阳戏却比较式微,阳戏不仅剧目短少,内容单薄,表现形式单一,就是在传承上也对阴戏具有严重的依附性,这就是所谓“阴(阴戏)盛阳(戏)衰”的文化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生苗”长期以来“信鬼好祀”的文化传统、战争及民族迁徙、边墙的修筑及“生苗”、“熟苗”的隔绝是密切相关的。
一
在边墙(南方长城)外围地区,民间戏剧按功能特征通常划分为两种:一是“阳戏”,二是“阴戏”,简单地说,阳戏是跳给人看的戏,阴戏是跳给神看的戏。在这一地区,跳给神看的阴戏至今仍占据着统治地位,而跳给人看的戏剧目少,剧情单薄,表演技艺不高。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这一地区在长达二、三千年的民族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一直沐浴在“信鬼好祀”的巫风祭俗之中,而巫风祭俗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祭祀活动,而在祭祀过程中用以娱神的戏剧、舞蹈被大量使用,也就是所谓的阴戏十分繁盛。
我们知道,今天生活在松桃全境及铜仁部分地区的苗族民众,是远古九黎、蚩尤、三苗蛮夷的后代,其祖先曾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有专家考证,蚩尤时代南方蛮夷的刑律制度、兵器制作等领域在中国大地上处于最高水平,在三苗时期,南方蛮夷的城市建设、医药等居于领先地位。从大量的史诗、祭辞及汉文献典籍的相关记载可知,祭祀文化是苗蛮部族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产生的娱神歌舞十分丰富。一部苗族古歌,就是一部祭祀文化史,记录着苗族人民到达每一个新迁居所进行的祭祀情况,例如,流传在黔东北、湘西苗区的古歌《鸺巴朵玛》前后就记述了苗族先民举行的数十多次祭祀活动之情况,其中,对于在“占楚占菩”(苗语地名,有学者考证为古代楚国某地,位置大致在今天的湖北中部一带)举行的祭祀活动,史诗是这样描述的:
“七宗一齐来到占楚
七房一齐来到占菩……
住了三年,住了五载
人数越来越多,
生活越来越好。……
于是,姊妹搓商,兄弟作议
商量要消祭祖
商议要制鼓集会
鼓社人山人海
鼓会歌声悠悠
男的四方拜朋访友
女的八面寻亲问戚……”
古歌中描绘的这种欢乐场面,充分反映了苗族在“占楚占菩”这个地方建立的远古文明所达到的繁荣景象,说明苗族古代的娱神歌舞或神戏艺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古歌反映的这种欢乐场面,与屈原《九歌》所反映的祭祀情况有异曲同工之妙。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认为:“九歌者,屈原之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歌舞之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而作九歌。” 这就非常清楚地指出《九歌》就是屈原根据楚地人民,其中主要是“信鬼而好祠”的苗族先民举行祭祀活动时为娱悦神灵而演出的歌舞内容改写而成的。
曲六乙先生在《漫话巫傩文化圈的分布与傩戏的生态环境》一文中说:“我认为《九歌》无论是整篇表演或是演出个别篇章都已具备歌舞剧雏形,至少处于歌舞到歌舞剧的初步过渡。但这不是一般常见的歌剧形态,更不是戏曲,而是初期的傩戏雏形,是从傩祀(傩歌傩舞)向傩戏雏形,是从傩祀(傩歌傩舞)向傩戏初步过渡的原始低级戏剧形态。”(摘自《中国傩》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东汉学者王逸及现代学者曲先生的精辟分析,使我们认识到,在屈原生活的战国时代,武陵五溪地区蛮夷部族的多神崇拜信仰和信鬼好祀之俗,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单一的原始祭祀阶段,发展到初步具有戏剧艺术因素的文化形态了。这从一个方面说明,“生苗”以娱神为目的的阴戏源远而流长,直至今天,我们仍可以用“九歌”与现在流行在边墙(南方长城)外围苗区的祭祀活动及阴戏进行对应研究。
正是苗蛮民众逢事必祭的文化传统,润育了边墙(南方长城)外围地区丰富的阴戏,以傩祭活动为例,10余种功能不同的傩祭活动,蕴含着50多个阴戏剧目,其中“五谷愿”(祈求五谷丰登)、“平头愿”(平息争讼由“人头愿”演化而来)、“子嗣愿”(祈赐儿女)、“长寿愿”(求长寿)、“过关愿”(儿童避关煞)、“平安愿”(祈病人康复)、冲“急救傩”(为病情严重者抢魂)、冲“太平傩”(又称“耍傩”)8种傩祭活动就蕴含近40个阴戏剧目,这些祭祀活动,涉及无数的祭祀对象,著名的有三十六堂神、七十二堂鬼,每一堂鬼神又分成若干支,每支又有若干组。大量鬼神在人们思想中的存在,被供奉,使得这里人们的祭祀活动十分频繁,“跳给神看的戏剧”也大量被创造出来。以至于在苗族社会生活中大到宗族不睦、争讼难息、出现盗奸、老人求寿、小孩多病、畜禽不旺、宅有不洁,小到遇见异象、眼跳耳热,等等,都要通过举行祭祀来加以解决,于是乎,整个族众对神灵万物的膜拜,形成了把祭祀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并积以为习,尉然成为人们心理趋同的“寓乐于祭”的审美情趣。这种民族心理因素反映到文化上,便显示出特别“信巫好祀”而轻“娱人”功能的基本特征。
可见,阴戏的兴盛,源于“生苗”区自远古九黎、三苗时代一脉相承的“信鬼好祀”的文化传统,而正是这种只关注人与神的关系,不关注人与人关系的文化传统和审美情趣,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娱人戏——阳戏的产生和发展。这就是苗蛮部族的娱神戏(阴戏)虽然早在远古时代就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始终未能产生出真正意义上以娱人为目的的阳戏之原因。
二
边墙(南方长城)外围原“生苗”区娱乐人戏(阳戏)式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苗族在历史上曾经历过长时间,大范围的迁徙,这种行无定踪、居无定所的生活状况,阻碍了阳戏产生和发展。
苗族的迁徙范围不仅遍及全国,也遍及世界,所以很多学者认为苗族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在中国古代,苗族迁徙的时间、幅度、范围是其他民族不能比拟的。《鸺巴朵玛》反映:苗族先民在“云梦云稀”、“云河云尾”一带曾过着鱼米丰富的日子,但平静而富足的生活不久就被打破了,三苗部落在战斗失败后,不得不举行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史诗唱道:
“鼓会没有完毕
灾祸从天而降
珈嘎钻进苗寨
珈狞钻进苗村
钻进苗寨来吞男
钻进苗村来啃女
……
鼓社成了魔社,
鼓会成了鬼会
……”
战败的苗蛮部族分成了两支,即仡熊和仡芈。仡芈留在原地接纳了一部仡扎(汉人),建立了楚国,仡熊一支则离开了原地,“向太阳落坡的方向前进”,沿途不断被人追杀。
据统计,从汉代伏波将军马援攻五溪苗蛮,到元朝末年,官府对苗区较大的军事行动达一百三十多次;在明代,自朱元璋登基到万历年间的二百多年时间,征苗剿蛮活动更高达三百多次。(见清人严如煜《苗防备览》)
自称仡熊的苗族族群,最后只得进入武陵五溪一带的崇山峻岭之中,这就是文献典籍中所谓的“红苗”。他们来到黔东北及湘西之间的山地后,前有思州、思南等大大小小的土司政权势力的阻挡,后有官府军队的不断征讨,活动区域已非常狭窄,生存条件也极为恶劣。
高压政策和险恶环境促使“生苗”在宋、元、明各个时期多次出现大分化。在宋代,分布在湖北、湖南一带的苗民首先被官府征服。湖北提刑赴鼎在熙宁初年(1068年)向皇帝上书中就说:“诸蛮荐饥,洞酋残刻,群思归化”。说的是一部分“生苗”归顺官府的情况;在元代,一些蛮方峒民在成为“熟苗”(归附官府之苗民)以后,帮助官府进入“生苗”之境赶苗夺业;在明朝初叶,“生苗”的活动区域从“凡思州、思南周匝二千余里皆红苗所据”(引自《贵州通志•前事志》)的黔东北全境、黔东南一部分地区,退缩到黔东北地区及黔、湘结合部地区;在明朝万历年间官府修筑边墙(南方长城)之后,“生苗”基本上从湖南境内退出,仅活动于黔东北以梵净山为中心的区域,在孜土归流前,红苗的活动范围又从“铜、思所属有梵净山焉,向为苗人所居”(引自《移建安化县碑》)的梵净山区域,被压缩到边墙外围区域,也就是今天松桃坡东、坡西地及铜仁市部分地区这一狭长地带。
“生苗”民众在被挤压在边墙外围区域后,仍然以武力抗暴图生存,官府在反复征讨无效的情况下,宣布“蛮夷内附无益,徒耗中土,宜择土豪立为酋长,借补小官,以镇抚之。以蛮制蛮,损虚名而收实利,策之上也”。派出人员在“熟苗”头人的引荐下深入“生苗”地界,寻找头人委以官位,实行羁糜统治,“羁糜者,以笼络之策,自外约束以不使心生异意也”。
“生苗”在历经数千年的大迁徙和一次又一次的征讨之后,人口急剧减少,生产力水平始终停留在极低水平,加上新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必须在陌生的、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从心理上到生活上都要承担战争、迁徙、饥饿、恐慌的新压力。
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及生活物资的匮乏,使得生存方式成了一个紧迫问题,在整个部族思维惯性的作用下,求助于超自然的神灵力量护佑的愿望越发地强烈,在这种生存景况下,祭祀更为虔诚,也更为沉重,有的人家,为了酬谢神灵,把家庭赖以生存的耕牛、肥猪椎杀,倾其家中所有,目的是求得神灵的护佑,给迷茫、无助的心灵一点慰籍和注入一线希望。基于一种本能的防范意识,有的仪式不能让汉族人观看,至今仍如此。
在这种心态和环境中进行的祭祀活动,便表现神灵为重人为轻,祭祀为主戏为辅的现象。整个部族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与先前相比,不是增强了而是萎缩了。这就是直到近代,在原“生苗”区仍未产生独立于娱神戏之外的真正意义上的阳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边墙(南方长城)的修筑及“生苗”被挤压在黔、湘边境狭长地带这一历史事件,对原“生苗”民众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影响,使得这一带的苗族民众在改土归流政策实施以后,乃至封建制度结束以后,对外界事物仍带有强烈的抵触、抗拒意识。
当黔东大部分地区、渝东南、湘西等地区阳戏蓬勃发展的时候,处于这些地区核心部位的边墙外围原“生苗”区,仍是“春风吹不到”,阳戏及其他艺术形式仍旧影响不到那里去,因之,边墙(南方长城)是阻碍原“生苗”区阳戏产生和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
明代万历四十三年,辰沅兵备道蔡复一主持修建了一条东起镇溪所(湖南吉首)西至铜仁亭子关的“边墙”(即“南方长城”),长达300余里;天启年间,辰沅参将邓祖禹受命将“边墙”自镇溪向东北延伸至喜鹊营,增加了60余里。这条横亘于湘、黔边境长达360多华里的边墙(南方长城),将“熟苗”和“生苗”隔绝开来,对“生苗”在政治上实行边缘化,在经济上、文化上实行隔离和封锁。
《戒苗条约》规定:“如有执刀行走者,即系逆苗,拿获定行诛戮。”“凡生苗轶入府县城或屯堡,擒送帐下,复缚虏囚,置高竿,集健卒乱箭射杀之,复剖裂肢体,烹啖诸将士。罪轻者裁去耳鼻使之去。” “生苗”区域在政治和人身自由上被加以隔绝,在经济和文化上受到封锁。
清初,凤凰同知傅鼐开始在苗疆广筑碉堡,设置营汛,到清中叶,官府在“生苗”区设置的营、汛、碉、堡、哨、卡等军事设施多达上千座。
明清设置在苗疆的这些军事隔离设施,尤其是边墙(南方长城),严重地隔绝了“生苗”与经济、文化相对先进的“熟苗”的交往,造成了同一民族不同地区的极大差异性,
当然,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边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止或延缓了发达地区汉族地主、奸商对“生苗”土地的豪夺和经济盘剥,使“生苗”得以在仅存的狭小地域内获得一定时间的休养生息机会和生存空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边墙的修筑,对保护苗族自身文化体系确实产生了意外的效果,边墙外围松桃坡东苗族聚居区,直到解放前夕仍称作“三不管”之地(湘、黔、川三省政府无法控制),这就使得原“生苗”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生活,从而保存了自远古九黎、三苗时代以来一脉承袭下来的苗蛮文化,包括独特的建筑、宗教、医药、婚丧礼俗等文化艺术,如花鼓舞、傩文化、苗族巫术、椎牛、接龙、收雷公、打棒棒猪、求雨、赎粮魂等,至今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朵奇葩,许多项目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但是,对于“生苗”与外界的文化艺术交流而言,边墙(南方长城)的阻隔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作用力是十分强大的。
清朝初年,官府开始在全国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到清中期,边墙外围地区有了流官进驻,湖南的辰河戏、渝东南的花灯、四川的川剧等艺术形式在“生苗”区的周边地区十分活跃,但以娱人为主要功能的阳戏并未在原“生苗”区相应地产生。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要求民众革除陋习,破除迷信,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一些从敌占区来的知识分子深入松桃城乡,唱抗战歌,演现代戏。在他们的带领下,松桃出现了一批有现代思想的青年,有的在地方服务民众,有的奔赴抗战前线。这一阶段,原“生苗”区开始出现一些现代歌谣和戏剧,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日救国,改造国体之类的。这一时期,一些原本从事祭祀活动,跳神戏的民间艺人,对神戏内容或形式作了局部的改动,把原本娱乐人的剧目,改为讽刺时政,诉说民间疾苦等题材的阳戏。其中,较有成就的是长兴堡的彭家班子,城关的龙家班子。松桃文化部门对之调查后发现,这些班子创作的阳戏剧目仍然不多,演出也多般是为宣传而进行的,没有进入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通常在宣传活动停止后这些剧目便被束之高阁,大多数没有传承下来。
解放以后,特别是1956年国务院批准撤消松桃县成立松桃苗族自治县后,原“生苗”区民众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指引下,在思想观念上走出了自我封闭的圈子,有不少人积极投身到包括阳戏在内的文化艺术领域的创作中去,创作出了一批有一定思想性、艺术性的文艺作品,但大多数作品以政治挂帅,没有成为有影响力的阳戏剧目进入民众的生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原“生苗”区阳戏创作和演出迎来了兴盛期,这一时期,许多民间艺人进行了阳戏艺术创作的尝试,题材大大地拓宽了,有的取材于文献典籍,或民间传说故事,有的取材于苗族神话、传说、故事或日常生活中的事件,较为成型的有《哨子打鱼》、《金花银花》、《补锅》、《仡索仡本》、《黄河造船》、《癞子寻妻》、《送郎参军》等等,此外,还从“三国”、“说唐”、“水浒”、“说岳”、“三女(龙王女、孟姜女、庞氏女)”等传统故事系列,或“谎江山”、“石柳邓”、“呆女媚”等民间系列传说中裁取一些片断构成小戏或小折子戏进行演出;这一时期,阳戏大多以灯戏的形式在公众场合演出,也有以愿戏的形式在民众家庭中演出,参加阳戏的人员以民间艺人为主,文艺工作者也时常现身其中。
近年来,由于农村人口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家乡涌入城市,很多民间艺术形式后继乏人。原“生苗”区无论是阴戏还是阳戏,都呈现萎缩状态。相关业务部门虽然在全力抢救,但由于起因是生产的社会分工的大调整、大变化,引起了文化环境的大变化,包括阴戏、阳戏在内的民间艺术都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其萎缩、分化、重新组合的过程将相当漫长,且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综上所述,原“生苗”区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民族独特的文化审美观,不断迁徙和经历大量战争的历史,以及边墙修筑这一特殊历史事件的出现,共同促成了这一地区长期以来阴戏盛行而阳戏式微的状况,在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这种状况在短期内将不会改观。(吴国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