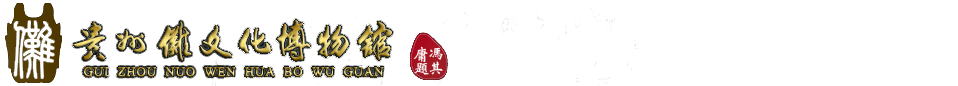傩与佛
时间: 2011-07-17 21:52:10 浏览: 6044如前所言,儒、道、释三种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都扮演过官方或主流文化的角色,而这其中唯有佛教文化来自外域。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既有着强大的拒斥力,同时又有着宽广的包容力,任何一种异域文化进 入中国,若不是被冷落或拒之门外,便是被传统中国文化改造而纳入华夏传统文化的体系。佛教属于后者,例如佛教禅宗化就是其被改造发展的例证。佛教东渐进入中国后,所经历的魏晋南北朝正是中国宗教历史上极为活跃的时代。梁武帝、昭明太子萧统等,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奉者和倡导者。史籍记载,梁代有佛寺两千八百余所,仅建康一地便达八百余所,可见其盛。然而与傩一类本土文化相比,其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的时间毕竟较晚,因而它一旦进入,便存在与包括傩在内的本土文化相遇国相撞的可能性。它首先必须使傩自己在内容和形式上适应本土文文化,以达到被接纳的目的,否则就有被逐出的危险。因而,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前期,不是佛对傩产生影响,而是傩以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去要佛发生认同于傩的变化。据王兆乾的调查和考证,安徽贵池在1949年之前有一种不太受戒律约束的"应付和尚",实际上就是由寺院出资培养的中国式傩师,专为农户请神打醮做法事,他们也能伸手下热油锅捞钱、走火砖等。应该说这正是傩影响于佛的证据。在敦煌卷子中,有许多宣传佛旨的变文与今日傩戏的语言。例如伯二一八七《破魔变文»: "伏愿长悬舜日,永保丰年,”、“…合宅小娘子郎君贵位。儿则朱缨奉国,臣辅圣朝","门多美玉, 宅纳吉祥,千灾不降门庭丕善咸臻门…城隍社庙,土地灵坛。"此类祈福之词,在傩祭的咒语和“吉断”、中随处可见。贵池傩中常有 "断" "感"之词,所谓"诗断”、 “社坛断”与敦煌卷子中的"断"、"感" 词的运用有很大渊源关系,甚至在句式、风格和内容上都十分相近。崇奉佛教为释家所称颂,又为贵池傩祭中一位地位极高的大神,在一定意义上可为这一时期储与佛之间这种相互影响的佐证。
傩与佛之间相互影响最明显的结果应是“寺院傩”,这一位住祭类型的出现。
所谓“寺院傩”,主要指藏族聚居区大寺院里的祭祀跳鬼活动,在藏语叫“羌姆”。在黑龙江省嫩江流域的蒙古族舞,则叫"查玛"。清代乾嘉诗人李若虚随军入藏后写的《西拓杂诗》中的第六首,描述过当时跳神驱鬼逐疫仪式的热闹场面,所谓"万口喧腾晌法螺,梵呗声中看大傩”。《历代咏藏诗选》 "梵呗"自然指佛教音乐,而“大傩”则是傩文化的祭祀类型之称。十分形象地描述了二者相互交融的情景。寺院傩,始至8世纪赤松德赞藏王为夺回权力和摆脱从吐蕃时即有的苯教巫师控制而强行推行佛教之时,他延请印度莲花生大师入藏修寺,将苯教仪式、傩面具舞蹈等溶入佛教金刚舞而创设了跳神活动。作为藏传佛教的一中祭祀仪式,寺院傩的流行基本上是为推行佛教文化而应运出现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正好证明是傩影响了佛。佛吸收了傩的内容和活动方式,使佛 事成为适应中国藏区人民传统文化特征的宗教信仰,而很难说是佛首先影响 了傩。各种类型"羌姆"中的神佛供奉、面具特征,包括拉萨每年"驱逐活鬼仪式"中的寺院傩,都是以宣扬佛法为根本,而在形式、手段上融入了傩和苯教的特征,从而形成与其他民族佛事活动明显不同的假面跳鬼,具有古朴、粗犷、狰狞和法术气息很浓的特点。佛教在传入中国前,早已是理论化、 体制化、周密化的宗教文化,其中进入中国后出现的许多独具的特征,无疑与傩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至于藏区所谓民间傩,如"米那羌姆"和白马藏人的"十二相舞"等, 则因与庙堂、寺院、宫廷的疏离,而更多保存了傩文化原始和民间的特点。 "十二相舞"在每年祭祀山神时跳,有"狮、虎、豹、龙、牛、 羊、豕(shi )、风、祭、大鬼、小鬼、丑莫(地母)"等十二种面具舞。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它与汉代中原储祭活动中的"十二兽舞"有某种联系。当 然,这有待继续研究。还有作为西藏民族戏剧的藏戏,在文化根源上无疑是佛、傩和苯教结合的产物,它在内容上佛教与历史世俗结合的特点是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在于它在形式结构和表演上与储及其他传统文化具有密切关系。藏戏中的"温巴顿"类似于"请神" "开坛”,而“雄”则如“正戏”,最后"扎西"就是"送神" "闭坛"了,而面具中神、人、兽的组合也与傩。
面具结构的多样性有内在联系。由于藏戏宗教与娱乐的双重功能及其与"羌姆” 的活动根源,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它视作傩文化对佛教文化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