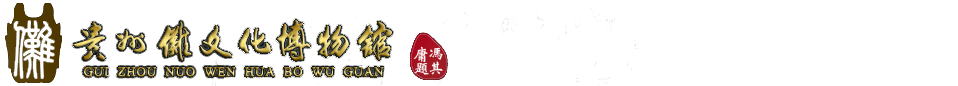傩的分类--寺院傩
时间: 2011-07-15 14:44:34 浏览: 16340寺院傩与军中傩在形式上有共同之处。军中傩是将傩中所含的"武事" 因素抽离出来加以强化,使傩服务于军事,从而逐渐独立为一种类型。寺院 和住则是将傩中所内含的"宗教"因素抽离出来加以强化,使傩服务于寺院,并同与之结合的寺院固有宗教内容相互渗透而逐渐独立成为某种特殊的类 型。它们的共同特点都在于请神驱鬼、祈福禳灾。比如道教寺院中的傩,比较突出地表现在醮(jiao)斋一类的仪式活动中,并在道教经典里多有记载。关于"醮”,《隋书•经籍志》这样解释道:
消灾度厄之法,依阴阳五行数术,推人年命书之,如章哀之仪,并具货币,烧香阵读。云奏上无曹,请为除尼,谓之上章。夜中,于是星 辰之下,陈设酒脯饼饵币物,历丰巳天皇太一,祖五星宿,为书如上章之仪以奏之,名之为醮。
在《道藏» "浻(jiong)神部•威仪类"中又将"醮"分列为自焦宅、瞧墓和解厄三类,并对供物、祭坛和招神做了详细规定,如其中的《正一醋、宅仪》指出,供神之物主要是绢布、果物、米、饼等。所招之神主要是五方室神、五七将军、宅内众官等。一旦把众神招请入坛后,便献上香、茶和酒,同时开始陈述俗界心愿。有意思的是这些陈述己事先在经典中准备完毕,成为一种规范格式,可供任何主持人使用,相当于早期傩文化原型中方相氏率百隶击 鼓大日子时所唱出的驱鬼歌,所不同的是方相氏之歌是唱出来惊吓鬼神,是唱给被驱逐的对象听的。而道教醮仪中的陈述之辞却是唱给所招之神听,是世俗之人向神界之灵的一种陈述、一种祈愿:[page]
伏愿神官普垂恩佑,请勒五方直符,为某驱遣宅内五虚六耗,萤尸邪魅,及咒时瘟疫炁 (qi),中外强碎,行客寄鬼,雄雌注杀,远去千里! 这类醮仪由于依附于道教,便随之流传到了后世。据记载,在中国的台湾省台南市,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时常举行规模盛大的道教瞧仪,也即是我们所说的"寺院傩"活动: 1979年年末的王醮,在公历四月十二日早晨举行了迎王爷仪式。四月十一日深夜,庙里亮起灿烂夺目的彩灯,一派辉煌,道士在醮坛上举行仪式。自醮坛是在庙的旁边特别装饰起来的,高功道士登上 庙庭中布置的坛,向神诵读叙述醮仪祭程序和目的的疏文,读后放到锅中烧掉,送上天去,之后,人们以神舆为先导,跨过熊熊燃烧的油锅,向着河滩迎王爷。祭礼的高潮是被称为宋江阵或称为村里的青年团的一队人,手持枪和矛等各种武器模型,身着一式服装,跟着神舆走到滩……表演威武雄壮的 舞蹈。童乩也登场,挥舞着刀和狼牙棒,背上流着血,假扮成神的样子,人们远远地把王爷船围起来。圈中童乩乱舞,神舆四处飞奔。不久,点火烧船。在村人们的守护之中,送走王爷,祭礼宣告结束。这个例子十分鲜明地展示了道教醮仪中所体现的寺院傩情形,同时又可略悉其在具体的操作中与民间傩相互结合的状况。在佛教文化中,寺院傩体现得最突出的应数藏地佛教里的"羌(qiang)姆"主主事和汉地佛教里的"目连戏"扮演了。所谓羌姆,是藏语对喇嘛教寺庙舞跳的称谓,本意为舞,后成为专指用于驱疫鬼、酬II神灵戴面具表演的宗教法事,相当于汉语俗称的跳神。羌姆产生于8世纪莲华生大师创造桑耶寺时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的特点是以人扮神,以神逐鬼。人扮神时头戴面具,手执兵器和总器,不断舞蹈,同时穿插着不少以佛经故事为题材的叙事性节目,并有怯螺、日唤日内、大鼓、长号等器乐伴奏,与道教酿仪所体现的"寺院傩"相似。佛教寺院傩也有一个与本土原生文化中固有的传统因素相结合的问题,因此也就涉 及到了有关孰先孰后孰源孰流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羌姆"傩仪的出现, 当在佛教传入西藏地之前,是吸收原有的苯教傩舞成分并加以改造、融合而 成为的一种专院傩。[page](曲六乙《中国各民族和傩戏的分类、特征及其活化石价值»)这种情况在汉地佛教搬演"目连戏"的现象中更为复杂。"目连戏",即 从佛经故事目连救母为题材改编而成的戏目。由于在慎出时间、地点及其规模和功能上的独特性,又成为了佛教讲经说法超度亡灵的一种法事和完整的戏剧目种。剧情为目连全家行善,其父病故,母刘氏因怒而焚毁佛经起,至目连救母出狱止,讲述了刘氏死后所经历的各种报应、灾难和目连为了救母而不避艰险、亲往西天求佛、遍游地狱寻母等情节。上演的时间通常是在农历每年的七月十五日,即佛教的中元节。按佛教说法,此曰"天堂启户,地狱门开,三涂业泊,七善增长"。因此,各寺院纷纷开讲《目连变文»,阐明因果,超度亡魂,从而使"目连戏"的演出成为请神逐鬼、祈福攘灾的宗教祭祀活动。同样,与道教醺仪相似,"目连戏"也由于附着于生命力强大的佛教传统自身而流传到了当代。[page]
1989年10月,在湖南怀化举办了一次"目连戏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与会者观摩了由当地群众表演的辰河高腔目连戏。其演出时间之长与规模之大表明目连戏至今仍颇具活力。日本学者做访春雄在讨论会上提交了论文《日本、中国、朝鲜的假面剧»,文中阐述了中国古代"追傩"时佛 教法事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傩与佛法先后传入日本之后的具体体现,其中尤其强调了佛教寺院因对"食住"的吸取和采纳而形成的一种现象,即修正合法事的历史意义,正是这种法事促使了"亡灵剧"或"鬼艺能" 的诞生,从而进一步促成了日本能乐的出现。 这种观点认为,"寺院傩"作为一种独立类型乃是一种后起现象,是 宗教对早期傩文化原型的一种接纳并融合的结果。至于"目连戏",有人看法则强调了其中所体现的宗教与艺术的 "互动"关系,认为其"既是佛教说法的产物,又是各种宗教祭祀礼仪的节目:既是中国戏曲慎变史的活化石,又是戏曲与宗教的血缘关系的标本。" (郭英德《世俗的祭礼--中国戏曲的宗教精神》)当然,这里所指的艺术与宗教不仅指特定的佛教或道教,而是泛指所有带宗教性质的超世俗现象,因而更接近"傩"的特质,因为"傩"的原型中本身就兼具着宗教与世俗两层意义,从中演化出独立的宗教类型--佛教或道教的"寺院傩”,看来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page]
除上述四大类型这样一种分类方式之外,我们还可以将中华傩文化在空间格局 上分为三大类型:即中原傩、北方傩和南方傩。这三大类型同样也可称作中原傩文化区、北方傩文化区和南方傩文化区。北方傩文化区主要属于黄河以北的草原地带,人们以畜牧方式为主,所使用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中原傩文化区与南方傩文化区在地理上分别属大河流域的平原地带矛"山地 高原地带,二者都属农耕文化类型,语言同兰陵王面具是汉藏语系。不同的是中原以麦作为主,南方以稻作为主;中原以儒为主,南方以巫为主。粗略来看,此三科类型大致分别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1、中原傩由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傩在中原受到了朝廷天子的高度 重视,一度成为国家性的大礼,在先秦时代几乎是压倒一切的主流文化。因此在从宫廷到民间,从军事到民事以及从宗教到世俗等各方面的分布上显得格外完整,在具体操作礼仪上也十分精致,并且规模宏大,传承可考,记载齐全。另外,"食住"这一概念无论究其字形、字音还是字义都可说完全是中原文化的产物。正是以它为核心、为标准,历代文人史官才陆续记载、描述和分析比较了中原之外的其他类型。
2、北方傩主要也就是指以往人们通常所说的"萨满"现象。"萨满"是通古斯语的音译,指一种神灵附体的人,能够为常人驱邪治病。现在人们常用"萨满"一词来指代一种信仰或一种文化,即"萨满教"、"萨满文化"。这种信仰或文化在中国主要流行于北方民族如满(17世纪前)、蒙古(13世纪前)、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以及东北地区的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族当中。此外在中国境外的亚洲其他地区和欧洲极北部地带,还有美洲的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最大特点与 前面分析过的中原傩文化相同,就是相信在世俗人间之外还有一个鬼神世界 的存在。大千宇宙一分为二,上界在天,为神所居,下界在阴间,为鬼魔和祖先所居,二者之间即为人界,是常人所居住的地方。三界之中,神界主宰一切,神灵赐福,鬼魔布祸,因此需要由人界与神鬼界之间的中介人物--萨满为之沟通, 请神逐鬼,祈福攘灾。(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在这点上,其与中原方相氏请神逐鬼、祈福穰灾的性质完全一致。也正因如此,我们才将其称之为傩的一种类型--北方傩。以往的学者仅抓往"萨满"这一称谓,把它视为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忽略了其与中原傩文化的本质联系及历史上的相互影响,若仅就史料而论,以《周礼》原型为代表的中原傩文化同北方傩文化似乎关系不大,各自独立,但如果再推及远古,中原三代以前的傩文化原型,无论在生存方式(农耕兼畜牧)还是鬼神崇拜方面都极可能与北方傩文化同属一类,甚至同属一个源头。换句话说,二者间的分离和区别很可能只是很晚以后的现象,当然对这个问题的确证还需要非常深入和广泛的考察研究,但无论二者同源与否,作为一种外在标记,"萨满"与"傩"都不过是对同一文化存在的不同解读而已。一个是北方通古斯语的称谓,一个是中原汉民族语言的符号。二者在本质上完全可以视为一类。在我们的论述 中,由于已经假定了以中原傩为核心这一前提,我们就很自然地把它们都统归于"傩"了。当然,这样一来必定也就会随之带来许多理论上无法摆脱的偏见和损失。这是应当慎为注意的。[page]此外,还应当指出的是"北方傩"虽以原来称作"萨满"的文化现象为主要代表,但决不就意味着除此以外不再有其他形态。由于中原傩文化与北方傩文化两大区域的长期交往,二者之间都相互吸收了自身固有因素之外的许多东西。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例如在清代,随着北方满族的入主中原,"萨满教"亦即"北方傩"中的许多跳神仪式也就堂而皇之地闯入了京城,进入了朝廷圣殿,乃至随着满人的迁徙而流入了边远地区。另一方面由于佛教向北方地区的传播,在蒙古 人中间就逐渐出现了原有的以萨满教为特征的"北方佛"之外的新类型。以 史料中所记载的百灵寺"禅木"活动为例,即可见出这种演变和发展。每年夏历六月十四至十六日,当地都要举行由喇嘛主持的"禅木" (即汉语的"跳鬼" )仪式,目的在于攘除不祥、预祝平安。届时要由一些喇嘛装扮鬼神,并使用各式各样的鬼神面具,同时手里拿着陆器和降魔宝剑,在鼓乐伴奏声中 手舞足蹈,捉妖驱鬼。而每至此时,附近牧民赶来,观者如潮,磕头点灯, 虔诚之至。这例子既可视为第一种分类方式中的"寺院傩"类型,更可看作是中原(或其他地区) 傩文化对北方傩文化区的渗透结果。而在此之中又还可进一步找到彼此交融后的若干新的变异和创新现象。作为相对稳定不变的 文化内核,"鬼神信仰"可以说是始终如一的,而由于其在空间、时代及宗教、语言、习俗等不同外象方面的移动,傩才不断呈现出自己的千姿百态。上 面这个例子中,百灵寺的傩现象就既有佛教寺院傩的种子,又有北方(萨满) 傩的因素,同时也包含了中原傩文化礼仪的影响,成为了一个复杂丰富的混合体。但其中的"鬼神信仰"及其所派生的请神逐鬼这一关键内核却牢固存在,否则也就不再是傩文化的范畴了。 [page]
3、南方傩南方傩主要是指包括了巫文化及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活动中请神逐鬼现象在内的众多储文化类型。与北方"萨满"现象相似,长期以来,南方文化就是与中原文化保持着显著差别并以巫鬼文化而著称的另一大区 域。与这一历史格局相应,在傩的分布上,也形成了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又一类型--南方傩。巫文化就是傩文化。在这一点土,我们的看法是,二者的关系与其说傩属于巫,不如说巫属于傩。因为作为→种完整的文化现象,傩包含了巫。这里需要稍加分析一下。后人谈到南方文化时的确常用"巫"来 概括。其实"巫"也不是南方文化的本称,而是来源于中原。以楚地为例,中原史官所言的"巫",楚人自谓为"灵"。对此,近人王国维曾有过论述。 他指出"古人所谓巫,楚人谓之日灵"。他举例说"«东皇太»曰:‘灵(匡鸯兮校月匠,芳菲菲兮满堂, «云中君》曰:‘灵连路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此二者,王逸皆为巫,而灵字则训为神。" (请•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这段论述说明了二者之间的甘古关系,即原本不同的称谓因学者的解释而发生了改换,而在这里中原以称"巫"替换了楚地的称谓"灵"。角度变了,名称也随之改变,而改变的根据在于学者对二者间内在相同属性的体 认和把握。这就是说,后人所习惯使用的"巫文化"之巫,也仅是→个可替 换的概念符号,而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即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傩"。进而言之,南方巫即南方傩,其属于台住在南方文化中的一种显象,一种变形和一种独特的称呼。除了"巫"之外,南 方傩类型中另一主要部分即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许多被冠之以"原始宗教"的请神逐鬼现象,例如苗族的"跳鬼"、布"送火神"、布依族的"法拉"崇拜、白族的"天鬼"信仰等等。其中较为突出的有被称为"东巴文化"的云南纳西族人的驱鬼活动。东巴文化有较完整的鬼神信仰体系,据统计,仅记载于其经书中的鬼神就有2400多个之多。其中,神居于天,主宰一切,鬼藏于地,能加害于人。而有神灵附则可代表神的意志,驱鬼镇鬼,消灾免祸。
关于中国傩文化在空间意义上的分类,以下章节还要专门谈到,这里不再展开。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的这种划分在理论上包含了对"傩文化"现象的比较与分析。所有这些都是相对而言,并无绝对界限,并且这种中原、北方和南方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中格局都是一个动态过程,其本身即在不断随历史的演变而转变。